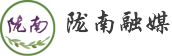蒹葭苍苍处,西汉水悠悠。
新月如钩映天幕,纤云散尽,飞星点点,南天门敞开。报喜的雀儿,成群结队,赶往河边,翅膀连着翅膀,搭起一座心桥。
牧牛的人儿,望眼欲穿。裙裾飘飘的心上人,踩着祥云来了,千山万水,两重天,银汉迢迢暗渡。西汉之滨,蓝天净,青草香,芦花白,芦花美。天上人间,双手合十,乞巧又一年。
秦风遗韵,梦悠悠,一梦数千年,千年祈愿汩汩流淌,汉河两岸泥里沉淀土里生长,梦里开花歌舞里徜徉。
水天缥缈处,伊人影徘徊。绣鞋浸满秋露,踩碎相思一寸又一寸。踯躅汉水岸,一步三回头,绸缎衣,绫罗裙,织锦衫。孤影低眉,双眸似水,满月的脸,桃花色,杏眼含羞,樱桃的嘴。发髻束起,云鬓高悬,点点花香发际绚烂。
蹙娥眉歌一曲,舒长袖舞蹁跹,撕开心结,解去重重锁,女儿心思谁了解!
(一)
七月,把祥瑞捎来了,乞巧的味道风里弥漫,一天浓似一天。
巧娘的影子在空气里播散,涂抹到村村寨寨,满树满枝,每一株期待盛放的花苞,笑意盈盈的,站立在六月的末尾、漾水河两岸、西汉水上游的村头,翘首期盼,那些山花正烂漫的甜蜜的日子。密密麻麻的心事布满村庄,忙忙乱乱的脚步踩乱女儿们的心房,叽叽喳喳的欢闹在青瓦木门雕花的窗里回荡。再严实的院落都关不住女儿们的心,她们掐指盘算,把七月遥望成一首小诗一叠画卷。
“女儿经,女儿经,女儿经要女儿听。第一件,习女德;第二件,修女容;
第三件,谨女言; 第四件,勤女工。我今仔细说与你,你要用心仔细听。”
木格子窗前,接过爷爷手中的发黄的小册子,毛笔的勾注评点爬满。八岁的黄毛丫头,挤眉弄眼,心不在焉,迷迷糊糊背诵着那些顺口溜似的经典,心儿却早早地翻墙越院,踩过青石板的悠长小巷,绕过曲曲折折的玉米林,穿过花香氤氲的篱笆围栏,在人群围观的打麦场上,在绿意掩映的核桃树下,跳进歌舞排练的队伍,和神采飞扬目光羞涩的伙伴一起狂欢。
“一根线,两根线,我把巧娘娘乞下凡。
巧娘娘,下凡来,给我教针教线来……”
母亲也不容许我去乞巧的!
参加乞巧前前后后将近一个月的时间,要集体排练节目直到深夜,太晚了还要到坐巧人家过夜,夜不归宿,家里人不会同意的;大部分暑假时间都耗费在乞巧这件事上,家里人也不会同意的。他们会布置更多的生字、成语、作文……没完没了的作业,枯燥得炸了头。出去玩一刻钟都要请示批准,晚一分钟回家都要认错挨训,每次都小心翼翼地羡慕那些伙伴,用尽心思将这些不同做过对比!谜一样的答案像天上的星星一样多一样遥远一样不确定。
可是,一场乞巧一次神秘的留恋,月容花颜的期盼!
记事起,就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在观众中亲历属于自己的节日,每一个女儿花朵一样绽放在生命的前台,自己却在人群中踮起脚尖默默注视,那些留在记忆中的画面,像褪了色的衣裳,是最爱,也是叹息!每次暗淡着目光走出人群,耷拉着脑袋回家,一声悠长的叹息像墙头的藤蔓,漫无目的的四处乱爬。
这一次,我要为自己做主,因为,八岁的小姑娘已经长大了!这一次,讨好似的提前完成所有的作业,预习了三年级语文课本的字词,拉拢伙伴们策划了一场周密的阴谋。先斩后奏!每每院边响起吹奏树叶的叽喳暗号声,我便偷偷溜出大门,飞一般地奔向坐巧人家,拿出跳舞的基本功向巧头儿毛遂自荐,主动要担任某个乞巧节目表演的主角,比如,《李彦贵卖水》,李彦贵假装卖水的担水于花园内,会见黄桂英一场,这是每年乞巧中的保留节目。主要情节是宋朝兵部尚书李绶被奸臣诬陷入狱,次子李彦贵因与黄璋之女黄桂英订婚,去投未婚妻家。黄璋见李家遭难,意图退婚。李彦贵沦落街头,卖水充饥,黄桂英见父趋炎附势,不肯退婚。后得丫鬟梅英相助,于黄家花园两人相见,并永结百年合好。“卖水哩……卖水哩……”,“卖水的,卖水的,我家姑娘叫你……”黄梅戏的曲调,节目就在婉转曲折的对话里开始,美好的因缘终以美好来结局。
再比如,《白蛇传》,前世善良的小牧童临危救难从捕蛇人手中救下一条白蛇,引发惊世骇俗的缘分,美好的姻缘,千年等一回!蛇经过一千七百年的修炼化为人形,为报救命之恩,经菩萨点化来到人间,变成美丽的女子白素贞,与前世的牧童今生的英俊书生许汉文,经历人间世事,演绎了一场恩怨生死,惊天地泣鬼神的爱情神话。“娘子……”、“官人……”,目光划过,俯仰之间,顾盼生辉。熟悉的唱词幽怨的曲调,梵音袅袅的仙界,青灯木鱼前,雷峰塔下,苦乐酸甜,风雨孤寂中的一对恋人,何曾对爱情有过一丝怀疑和动摇!十年修得同船渡,百年修得共枕眠,不曾修行的人,哪有什么机会和资格擦肩或者回眸?真正历经悲喜折磨,苦苦修行,在人世间相遇又彼此对视过并同船渡共枕眠的人,又会何等珍惜一份前缘?能否相偕白首,共度余生,似乎都已不重要。如今当便捷的爱情快餐布满大街小巷,我还是对那些留在幼小心灵里的美好故事更加喜欢。
还有一个家喻户晓的主题节目《七仙女》,天帝最小的女儿,聪慧巧手的织女;农家受苦的男子,善良淳朴的牛郎,他们本是天上人间仙界凡世,两相隔,一朝相识,坠入爱河,在烟火人间男耕女织,生儿育女。可惜美好的爱情好景不长就天各一方。
天上多了一把银簪,世间多了一道天河。织女被带回天界,牛郎身披织锦衣以腾云驾雾,忠贞不渝的爱情感动了天上的生灵, “鹊桥”,成全着牛郎织女一年一度的聚首。年年七夕,牛郎的扁担托起一双儿女,在爱情的路上星夜兼程,信守爱情承诺的织女,守望在河边,把自己站成一尊雕塑。故事流传千年,爱情从不变卦。可是某一天当爱情被物质的繁荣添加了诸多附属条件,城市的高楼迷失了男欢女爱的双眼,金钱的诱惑销匿了爱情的过程,钢筋水泥的大桥也承受不住轻如鸿毛薄如蝉翼的所谓爱情,他们还不曾走过这座神圣的桥就各自回了头。物质外壳下住着的又会是怎么样的爱情传说?好就好在,物质文明进步了,那些美好的爱情故事依然在脑海里刻着,以最初美好的样子美好着!
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是主要用纸扇表演的一个节目。唱词“祝英台,女扮男装学文化”,大概经过山村老人的改编,很通俗了。西晋时青年学子梁山伯辞家攻读,路遇女扮男装的学子祝英台,两人一见如故,志趣相投,于是结拜为兄弟,一起读书。三年的朝夕相处,感情笃深。分别在即,山伯十八里相送,二人依依惜别。蝴蝶玉扇坠的信物指点了山伯到祝家求婚,遭家长拒绝,他悲愤交加,一病不起,而后不治身亡。英台已被另许马家,闻噩耗而悲痛欲绝,迎娶的花轿绕道至梁山伯坟前,英台下轿,哭拜亡灵,因过度悲痛而死,惊雷裂墓,英台入坟。梁祝化蝶双舞。世俗的偏见不能成全一桩美好的姻缘,凄婉的爱情化作飞舞的彩蝶,爱的箴言只存在于自由的天空,它所路过的地方,必然花香鸟语,一路芬芳。
那些美丽的神话和美好的故事,除了可以在墙画和橱柜里的彩图上看到零星的故事片段之外,再没现成的具体画面,经由村里的老人口口相传,姑娘们自编自演成的一个个节目却烙印一般刻在脑海深处,故事情节在想象里不断延伸进而变得越来越清晰,在没有黑白电视的村庄,所有的故事内容都凭借想象演绎成彩色的画面。以至于后来读相关故事的文字,脑海里依然浮现的是儿时的场景:新月如钩,镶嵌在深蓝旷远的天幕,农家小院,树影晃动,晚风轻拂,月光把冰冷的蓝光涂抹到姑娘的发梢、眼眸和鼻尖上。借着月光和想象排出一个个故事情节,凄婉的故事凄婉着,柔情的故事柔情着,美好的期盼美好着!在一支乞巧队伍当中担任了某些角色的表演,叫做“装了身子”,装了身子的姑娘如同获得一份荣誉。偷着去参加乞巧,回家必然会挨训受罚,或者遭受阻止,装了身子就不一样了。伙伴们集体出动,七嘴八舌地游说,巧头儿巧言善辩,一番说辞最终还是成功将我拉回乞巧队伍,装了身子的我就得到巧头的重点保护了!
能名正言顺、光明正大、理由充分地参与乞巧,八岁的幼小心灵里除了开心,似乎天下再没有什么烦恼了。斗智斗勇共赢得的两次参与乞巧活动的机会,珍贵得如同一张儿时的老照片,夹在老屋某个角落的相框里,在落满岁月浮尘的光影里,美好的时光就此定格,不可复制,无法重现的美,永久刻印在心间,在岁月深处泛着亮光。
(二)
365日的翘首期盼,似乎都是为一个盛大的节日而做着准备。
四月的风,把指甲花的种子顺着墙根撒,红的一行,白的一行,粉的再一行。
五月的雨,一层一层飘洒在墙角的嫩叶上,一瓣叶,两瓣叶,尖尖的芽儿修长的杆,长成想象中的俏模样。
六月的阳光,透着露珠,渗着汗水,把麦穗变饱满变金黄,顺便把密密麻麻的花苞挂在指甲花的枝干上,在夜间一一盛放。
来不及了,来不及了,掐着指尖盘算,七月,七月在望,女儿们的心慌了,乱了,七月之前,一切都紧锣密鼓了。
赶紧包指甲。
弯腰在花畔畔,一手提着竹花篮,一手舞动花丛间;胖胖的花枝,水嫩的叶,三色的花朵儿,笑意盈盈的脸。一朵朵,一瓣瓣,挑花了眼,采来满满一篮。
在浊水里淘,在清水里洗。案板上切成碎末末,撒上矾,捣碎了装进小瓦罐。
核桃叶子摘一捧,浊水里淘,清水里洗,一片片晾满竹箩筐,一根线,两根线,红丝线,白麻线,丝丝缕缕牵着心里的乱。
剪指甲,修指甲。等日落,盼天黑。修长的手指伸出来,昏黄的灯影里头抵头,指甲花药指甲上盖,层层包,细细裹,一根线儿缠八圈。绑得紧,扎得牢,捆住手指,才能包出好看的手指甲。
核桃叶子,将凤仙花裹在手指上,酸涩的气味在小屋里弥漫。小心翼翼放置两只手,迷迷糊糊进入梦乡。梦里,指甲开了花,染着花的颜色,飘着花的芬芳,歌舞在指间荡漾。
夜半,花药渗入皮肉,渗入骨。针刺一般的疼,十指连心的痛,牵着七月的期待,心事装满梦里的甜。
天微亮,借着晨光,卸下手上的壳,十指发白,指甲橙黄,一抹嫣红,七月的颜色涂抹在心上,一朝破茧,蝶舞绚烂。
再包一次,指甲的颜色更红一层。
七个夜晚的疼,换来十指嫣红的花,盛放在七月诗意流淌的指尖。
每一个舞姿,都飘散着指甲花的味道;每一个眼神,都在彩色的指间点染。七月,每一个角落都绽放着指甲花的容颜。
七月去了,八月来,女儿们的心事,指甲一般,层层堆积,层层长出新的样子,指甲根露出一弯白白的新月。旧指甲被一次次修剪,只剩下一弯红红的月牙儿,垂挂在指尖。
清亮的河水里,美妙的诗意晨昏相伴,汩汩流淌。白皙的手指,红红的指尖,浣洗的身影越拉越长。
(三)
爷爷说:“女儿经的第四件就是勤女工.…..”
勤女工,要记清,起早莫到大天明。
扫地梳头忙洗脸,便拈针线快用功。
纺织裁剪皆须会,馍面席桌都要经。
描花绣彩皆女事,不可一件有不通。
我说:“巧娘娘都教给我了!”
“我把巧娘娘坐桌上,巧娘娘给我教文章。
我把巧娘娘坐桌前,巧娘娘给我教茶饭。
巧娘娘,下凡来,给我教针教线来。”
母亲每每擀面的时候,我在一旁静静观察。
十二岁,踩着小板凳做手擀面。雪白的面粉倒进瓷盆,适量的碱面,温水调和,柔软适中的面团,揉了又揉,直到光滑圆如满月,手拿擀面杖,一圈一圈地擀开,直到铺满整个案板,薄厚均匀,仍然是一个大大的圆。稍稍晾一晾,折叠起来,切成宽窄匀称的面条,薄厚宽窄均匀的面条,煮到碗里,端上堂屋的饭桌,奶奶的夸赞声便在屋子里荡漾,心头有股温热的暖流在奔涌,身体两侧生出一对翅膀似的,飘忽的身子飞一般穿梭在屋檐下的走廊。一双小手能在农忙的六月,擀出供家里8个人吃的面,像一个小大人一样分担着麦收时节的忙乱。几个六月过去了,村子里的人都知道我的手擀面做得好。行走在村边的小路上,在大柳树下,大人们在悄声谈论,我一脸镇定缓步经过,脚步忽然就变轻快了。
村里的巧婆婆家里,摆满了各式的绣鞋垫和绣花枕,姑娘们都请她在鞋垫上画上漂亮的图案,再穿针引线,将七彩的丝线绣成美丽的牡丹、双栖的鸳鸯,还有龙凤呈祥!学着她们的样子,在某个寒假,在冰天雪地的腊月,拿着寸把长的针,开始绣一树梅花。玫红的骨朵儿,淡黄的蕊,棕色的枝干,盘曲的形状。村里的女儿都完任务似的赶制鞋垫,绣不尽的鸳鸯枕,据说她们在积攒嫁妆!灵巧的双手还没有练就,就去上高中了,以后再也没有机会去绣花,只是拈针引线将心思具体成美妙图案的那些往事,风景一样刻印在心底,是巧娘娘教的针,是巧娘娘教的线。针针线线就在时光里沉淀,我知道,用绣花针一样的心思,去做人,去做事,去作文,在细小的针脚里,密密麻麻绣满路上的脚印。
新婚后的第四天,按照习俗,新娘子要做一顿手擀面,请亲戚朋友一起来,一者认认亲戚,二者试试手艺,叫试刀面。面擀得怎么样,刀工怎么样,这一试就真相大白了。公公婆婆庇护我,觉得我读了十几年的书,不为难我,就说:“你是公家人,不走老规矩了。”这一关就顺利过了。某一天,家里来了老亲戚,他们聊家长里短,晚饭时间,我把亲手做的擀面端到桌前,那位亲戚吃完面,高高兴兴走了。家里人也高高兴兴说:“显手艺了!”心里便暖暖的,自认为不足挂齿做法简单的手擀面,竟然成了一种好手艺。如今大街小巷摆满了各种各样的机器面条,匆匆下班的人们,排着队去争抢着买,老人们说:“生活太好了,啥都能买!”
在啥都能买的好生活里,我还是喜欢在比较悠闲的午后,将雪白的面粉和成柔软的面团,揉了十次又百次,一圈圈地擀开,薄厚均匀,切成细长的面条,宽窄合适,劲道的面,就是我的好手艺。或者,用传统的方式,发一盆面,蒸一锅花卷,一层又一层的花,卷着飘香的味,有着麦子的清香和指尖的温暖。在一个个流水一般的日子里,在机器面和机械化的雷同制作面前,唯有那些手工像往昔村庄里脸蛋嫣红的淳朴村姑,她们不化妆,不添加某些人工色素,一人一个面孔,各人有各人独特的美。
“生活的确太好了。”虽不需纺线织布,虽不需裁剪缝补,但也拥有一个针线盒,大针小针,七彩的线,亮晃晃的顶针,小巧的剪。大人小孩的衣物,若有边角开线,一针两针,学着母亲的样子,做一点母亲一般的针线活。慈母一样,把灯光和体温密密缝进,把手工做成一首一首的小诗。
这都是巧娘娘教我的!
(四)
二十余年过去,七月的风一次又一次吹醒潜藏在心底的牵念,心儿一回回游走,在印满童真的小径上徘徊。
这个七月,我做好了一切准备,去漾水之畔、西汉水滋润的土地,泥味草香里,看云,看花朵盛放。脑海里充盈着遥远的祈愿,内心浅吟低唱着巧娘娘的歌,身心沐浴初秋明亮的阳光,在一片风清气爽里,接受蓝天绿树的包围和淳厚的人情温暖,携着一份闲适几分憧憬无边激动,缓步行走在漾水河畔、晚霞湖水天一色的土地、汉河两岸草深叶茂苹果飘香的村落,去找寻蒹葭苍苍伊人飘忽的远方,去寻觅佳人遗留的踪影,去循着巧娘的指点引领,去熏染织女的灵巧聪慧。
点一支长香,举过头顶,一缕青烟在巧娘娘面前缭绕。一拜,再拜,凝神,期望,让愚笨少一点,祈求天上的仙女能给天下的女儿们好手艺,赐予贤能的心和如水的好容颜。
飘飘渺渺水草丰茂的西汉水上游两岸,每一寸土地的肌肤被歌声浸染,每一片摇曳的绿荫被舞姿陶醉。那绿树掩映的悠长的小路尽头,一串笑声一路欢歌一支彩色的队伍从蓝天白云里走来了,从秦汉走到明清,把古代走成今天,两千年的路上,咏唱声声诉尽女儿心头的望想。手中的红纱巾把小路染红了,芬芳的纸扇遮着脸,巧芽儿的芊芊玉指,巧果儿姿态万千,嫩生生的眼眸顾盼,彩蝶纷飞萦绕在身边,绚烂开在心间。
汉河两岸,漾水之滨,大地沸腾。
把乌黑的长发梳成花辫,用红丝带装点搭在胸前,略施粉黛,描眉画眼,涂上红红的唇,镜中映出容颜似水笑靥如花的脸。穿上布满牡丹花的红衣衫,手工的斜襟盘扣缀满,一只只欲飞未飞的蜻蜓,玲珑精致,是古老的中国结一颗颗,折叠盘绕出一针一线的思念。
彩色的队伍一排排,拜祭的香盘双手端起,香蜡果品贡放成满满的心意。扯下一片云,花朵捧在手里,纸扇捧在手里,女儿们虔诚的心捧在手心里,巧娘娘坐着花轿来了,云里来,天上来。歌声漫过西汉水两岸,漫过群山,漫过天河,黝黑的天幕静谧成六月三十的默默祈求,巧娘娘顺着歌声来了,踩着祥云来了,看,她慈眉善目,笑意盈盈,飞落人间。女儿们跪拜,烟火升腾,鞭炮齐鸣,欢欢喜喜的,把巧娘娘迎上走!
村庄的盛大节日拉开帷幕,一切都退居台后成为配角,女儿们属于舞台之上的主演。四岁的小丫头来了,满头的牛角,稚嫩的脸;豆蔻年华的姑娘来了,莞尔一笑青涩华年;年轻的村妇来了,抛却偏见尽情展现;花甲之年的老妇来了,一头银发红润的笑颜;98岁的老寿星来了,鹤发童颜,甩开龙拐开始三寸金莲的表演,扭动着沉淀在心底的欢。掌声响起了,欢笑声把村庄浸透了。刺绣的媳妇来了,做手工编织的老人来了,说着普通话的远方的客人来了,村委会的大喇叭里传出支书关于乞巧的宣传,欢歌笑语在村庄里蔓延。
取一碗晨曦里的神水,贡在巧娘娘的莲台前,受着天地香火的熏染,夜里借着灯影,投进巧芽儿,红豆芽,绿豆芽,黄豆芽,玉米芽,燕麦芽,一瓣、两瓣,三四瓣,投进清水的碗,巧芽儿开花了,开成了针线,开成了牡丹,开成了笔墨纸砚。照一照花影,照一照来时的路,照一照前世今生,照见了未来的花团锦簇。照见了人生的苦乐酸甜,女儿们笑了,喝一口神水,做一个美梦,向着那一片美好,踏踏实实地,修行着自己的灵和巧。
跳起来吧,跳一跳,跳起来就能让巧娘娘知道。麻姐姐,你来了。你在飘忽的灯影里来,顺着女儿满脸的汗水泪水来,在哭声里来。你来了,从另一个世界来,说一说这个世界听不到的话,透过你的神秘,来听巧娘娘的教导。让心中的女儿神开口说话,让内心的迷惑得到解答。“麻姐姐,你干啥着哩?”“织布着哩”;“麻姐姐,你干啥着哩?”“绣花着哩”;“麻姐姐,你干啥着哩?”“煨茶着哩”;“麻姐姐,你干啥着哩?”“擀面着哩”……世间的粗茶淡饭,粗布衣衫,柴米油盐,散着清香,透着温暖。麻姐姐,你快快回,你今年去了明年来!
年年有个七月七,天上的牛郎配织女。
一弯新月在高蓝的天幕静静守候,天河就横亘在面前,南天门,你何时打开?把我的巧娘放进去。普天下的女儿,都跪拜在河水流淌的岸边,眼眸含恨,手捧香蜡,捧着巧娘娘,捧着心中的女儿神,在夜色笼罩里,在暮色霭霭中,在迎她来的地方送她走。和心中的女儿神作别,长袖飞舞,离歌满地,一曲又一曲,离歌唱罢尽情舞,柔情舞尽默无语。秋风起,泪眼婆娑,此去又是天地相隔,何日是归期?再等明年七月里。巧娘娘,还是舍不得你走。天地昏暗,水无语,静静流过,女儿眼帘低垂,风吹芦苇窸窣。成群的喜鹊赶往那缥缈的河边,牛郎挑着一双儿女望眼欲穿,天上云聚云散,聚少离多又一年,赶紧送巧娘娘上天去。
把红手襻系在一起,把红丝带系在一起,把红纱巾系在一起,把纸扇搭在一起,把纸花堆在一起,把乌黑的辫子连在一起,把女儿们的心凝在一起。双手合十,在漾水河上搭一座桥,在西汉水上搭一座桥,在晚霞湖上搭一座桥,在天河上搭一座桥,在心里搭一座桥。三刀黄裱一对蜡,巧娘走家我咋家?巧娘娘,跳进火海里了,爱的火焰一经触摸到纸裙子,就在今夜,在女儿们面前,在无边的歌声和哀怨里,她瞬间将变成灰烬。她赴汤蹈火去了,火海里的巧娘娘,仍然面带微笑,面若桃花,巧笑倩兮,美目盼兮。巧娘娘浴火重生,凤凰涅槃。火光映红的天地间,她赐予人间灵巧、聪慧和美貌,再看一眼巧娘娘:巧娘娘眉毛弯又弯,杏核的眼睛圆又圆。线杆鼻子端又端,糯米牙齿尖又尖。带上最美的微笑和柔情,去赴一个千年的约定,千年的承诺就在每一个七月一一兑现。巧娘娘,你伴着歌声走。
“南天门,你打开,把我的巧娘放进来。巧娘娘,上天去,再等明年的七月里。”
歌哭散尽,声已远。
蒹葭苍苍,白露为霜,所谓伊人,在水一方。
年年七月,漾水之滨,汉水之畔,晚霞湖柔波荡漾。
莫相忘,伊人歌舞巧梳妆。
作者简介:
吕敏讷,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,鲁迅文学院首届自然资源系统作家研修班学员,陇南市作协理事,中国自然资源作家协会签约作家。散文作品见于《大地文学》《时代文学》《延安文学》《青岛文学》《鹿鸣》《飞天》《延河》《东渡》《岁月》《散文选刊》《海外文摘》等。有作品获奖并收入年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