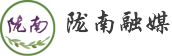丢了的时光还能回得去吗?儿时的年味儿你还记得吗?或许,时光一去不复返,但那些记忆深处的年味儿,像一张张收藏已久的老旧磁带,不经意间就会在某个时间、某个地点,勾起你的回忆……
小的时候,过了腊八,母亲就开始置办年货了。今天去城里买粉条,明天去城里买白菜,后天去城里买瓜子和糖……一样样地置办齐全了,差不多都到了腊月二十几了,哦,这个时间还不准确,有可能腊月二十几母亲还会去城里置办年货,因为过年的吃食要好,缺少某一样东西可能这个年就过不踏实。一年的辛苦就换来这么几天的安逸,怎么能让这个年过不踏实呢?即便明天就是腊月二十八了,也得去城里置办年货。母亲的倔强与生俱来,没有谁能够轻易改变她的决定。就是因为家里有这样的母亲,我们小时候每一个年都过得很踏实。

母亲置办年货的某一天,总会带着我和弟弟去城里的,那一天就是要给我们买新衣服了。我和弟弟兴高采烈地一路奔向城里,跟着母亲,一个店一个店地挨着逛。那时候,城里的一切都是那么新鲜,虽然每天来这里念书,但到了年关买衣服的时候,总觉得城里多了某种特殊的气氛,心里也总是喜滋滋的。那个时候只是知道要过年了,大街小巷才会这么拥挤,才会充满那种特殊的气氛。记得那一年,过年时候我穿了一套大红带有花纹的衣服,戴着一顶花色条纹帽子,身材高挑,走在同伴中间,显得格外耀眼。那种得意和兴奋就来自于腊月三十穿上新衣的那个时刻。那种特殊的气氛也在那一刻,无限放大,以至于无法形容出内心的高兴。直到现在,当这个城市变得越来越繁华的时候,当我时不时会回想起儿时过年的情景的时候,我才明白,那种特殊的气氛就是武都的年味儿,也是我们骨子里关于过年这个习俗的传承。
几乎每年到了腊月二十四这天,母亲一大清早就起床开始收拾厨房。我和弟弟永远是母亲的“得力帮手”,帮着母亲把锅碗瓢盆搬到院子里,母亲就拿着长长的扫帚,站在凳子上,一一清扫在屋顶堆积了一年的煤灰,所以这一天称之为“扫煤”。从厨房的顶棚开始扫起,到墙壁,到灶台,到地上的每一个犄角旮旯,再到客厅、睡房,从早上扫到下午,整整忙碌一天,这个灰尘才算彻底清扫干净。母亲总是会说一句:“赶紧认真扫,去去今年的晦气,让来年过得更好!”有什么霉运、霉气,在这一天扫一扫,一切都会好起来!这是母亲从小留给我们的生活箴言:霉气一扫,新的生活准来到!

过了腊月二十四,母亲的每一天都安排得很紧凑。那几天里,至今让我记忆犹新的事情就是杀猪、煮臊子,还有隔天母亲做的酥排骨。杀猪这天,天还没亮,全家人就已经迎着月色,呼哧呼哧地奔波在去圈里的路上了。这是早上杀猪之前最大的任务——挑水!父母亲挑着水,走起路来脚下生风,赶着时间能多挑一担是一担。我和弟弟一人背一个三十斤的塑料桶,也匆匆地踏着父母的脚印,瞅着他们的影子,浮动在路边的枯草上,一路跟回家。杀猪匠大概在早上八点左右来,一来先喝上三两酒,再饮上一杯茶,拿出磨刀石,“嚯嚯”地磨几下,就提着刀,淡定的走到猪圈那边去了。我们一帮孩子又怕又喜欢看热闹,跟在几个大人的身后,远远就听见猪歇斯底里地吼叫声,这个时刻总是那么惊心动魄,一阵惊魂的吼叫声过后,就只听到“嘶——嘶”地喘息声了,偶尔猪的某一只蹄子还会弹几下,那已经是它生命里最后的挣扎了,等到它一动不动时,一切都归于平静了,剩下的就是“人为刀俎,我为鱼肉”的无奈了。有时候,真想为这苦命的生命感叹一句,可是又有谁逃得过命运的劫数呢?最后,还是选择无言以对,选择认命,或者选择妥协,生命的无奈才是真正的无奈吧。

我们一帮孩子最喜欢看给猪开膛破肚的时候,我们的眼睛都是定定的瞅着杀猪匠的刀,它割在哪儿,我们就盯在哪儿,总感觉那猪的身体里藏着许多秘密,随着杀猪匠的刀起刀落,一一为我们解开了谜题,那股子好奇劲儿别提有多浓厚了。
盛了猪血的母亲已经在厨房忙得不可开交了,她要很快地在猪血里拌入荞面粉、调料,迅速搅匀,在煮沸的锅里,将其倒在箅子上,大火蒸一个小时,这就是母亲做的“血馍馍”,刚出锅时热乎乎的吃上几口,想想都觉得美味可口。哎,但那热乎乎的血馍馍总会被母亲切一块后,先供奉在大厅的上席了,因为要祭奠之后才能吃。这是习俗,要将第一块血馍馍和在沸水里煮过的肝心肺供在上席,等祭奠过了才可以吃。
这一天我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帮母亲切肉,将卸好的猪肉切成一个个小块,等午饭后就要放进锅里开始煮臊子。母亲煮臊子很讲究火候以及放瘦肉和调料的时间,一般一锅臊子要煮好几个小时,有时直到半夜才停火,这时锅里的臊子冒着小气泡,盛一些到碗里,肥肉看起来透亮,瘦肉粘着肥肉,放进嘴里,软糯糯的,肉香顷刻溢满唇齿间。我和弟弟还会央求父亲切一些瘦肉丁,拿着母亲织毛衣的棒针将肉串起来,放在火上烤着吃,那个“呲呲”的声音响起来时,肉的美味已经让我们迫不及待了。
杀猪的第二天仍然很忙碌,父亲要清洗猪肠,还要熬制,母亲开始准备酥排骨了,这也是我过年的时候很期待的事情。母亲将洗好的排骨沥干水,撒上面粉、淀粉,再放入各种调料,打入鸡蛋,便下手捏匀,之后一块块夹入油锅,炸至金黄,捞出即可食用。我这个小馋猫此刻是不可能离开厨房的,等排骨捞出来的那一刻,我总是第一个拿起一块,放进嘴里咬动起来,那香味儿,永远铭记于心。那不仅仅是一块儿排骨的香味儿,还有我儿时的幸福!仔细回想一下,住到城里以来,好像已有四五年没有吃到母亲做的酥排骨了,到底还是生活变了。

腊月三十这天,父亲早早地就开始贴春联、挂大红灯笼了,来年的幸福都印在了崭新的对联和那个高高挂起的大红灯笼里了……

置办年货、扫煤、杀猪、做各种美食、贴春联、挂灯笼……一件件小事里都蕴藏着武都的年味儿,无论你身在何处,你都会在某一个固定的时间里去做各种与年有关的事情,这是习俗,是深入到每一个人心里的东西,我们无法改变,也不会改变。

有了年,那些儿时的记忆就像那磁带里的某一首老歌一样,听一次,就回味一次;有了年,武都这个大家和生养在这片土地的千千万万的小家紧密相连,生生不息!
作者简介
李芳利,笔名一叶舟,甘肃武都人。武都区作家协会会员,文学爱好者,现任教于陇南市武都区鱼龙初级中学。有部分作品在报刊及网络公众号平台上发布。